 《财产权利的贫困:中国传统民事法研究》,邓建鹏著,法律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6.00元
《财产权利的贫困:中国传统民事法研究》,邓建鹏著,法律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6.00元
1853年6月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东方社会(指土耳其、波斯和印度斯
马克思为什么认为“东方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作者指出,原因在于私有制和私人所有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命题,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东方社会一向缺少私人所有权的法律观念。“所有权概念并非由传统中国法律制度所创制,这一概念是在清末法律制度改革中引自于欧洲大陆法系。其起源于罗马法,指所有人除了受自身实力和法律限制外,就其标的可以为他所想为的任何行为的能力。从消极方面讲,所有权可以对任何人主张排除对所有物的干涉。因此,所有权意味着绝对性、排他性、永续性的财产权利”(第14页)。英国普通法虽然没有像大陆法系的所有权概念那样的实体权利概念,但通过完善的救济诉讼制度,私人同样可以获得对于具有绝对性、排他性、永续性的财产权利的保障。反观传统中国,以皇帝为代表的王朝才是私人财产命运的最终决定者,王朝动辄可以籍没家产、超额征敛赋役、掠夺私人土地、制止私人贸易,等等。“在中国历史上,财产权从没有成为法律的抽象而排他的权利,政府没有义务在‘个体’的意义上保存社会成员的财富和财产权利,只是在‘群’的意义上保存人的延续”(第28页)。――而“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来自于对政权任意侵夺私人土地利益的制度性防范。如果不经权利持有人同意,权力机构或特权者就可将私人利益没收,比如不支付任何对价或者支付的对价完全不均等的‘国有化’,那么,这种土地‘私有’只是一种表象”(第53~54页)。
然而,1949年以后,国内的普遍观点是将商鞅变法以降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定性为“以地主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私有地制”(第12页)。这种与马克思本人的看法明显相悖的观点之所以能够长期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在国内定于一尊,自有其现实政治的背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土地改革等各种政治策略强化了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的对立。在阶级斗争理论下,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成为旧中国的主要矛盾”(第92~93页)。――可是,政治归政治,“政治策略的需要与历史真实并不总能保持一致性。源自于西方的理论忽视了地主在传统中国并不作为一个利益联盟的稳定阶级而存在,地主、农民与王朝(即民与官)的矛盾远远超过了地主与农民间的矛盾。更值得注意的是,自耕农民与地主间并不发生经济剥削关系,地主与佃农才存在矛盾,但佃农只占农业人口的小部分。”(第93页)前述“普遍观点”的立论基础是将王朝视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从而由王朝的专制权力推导出“地主阶级”是传统中国土地私人所有权的权利主体。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代王朝不但没有处处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相反,大量地主、富人(包括大商人这种通过求田问舍成为地主后备力量的阶层)备受王朝的打击”(第64~65页)。由于专制王朝对私人财产的掠夺,导致历史上大多数在今天被冠以“农民起义”之名的暴乱恰恰来自地主阶层的领导和筹划。“尤其值得现代学者注意的是,儒法诸家论述各种思想时,从来没有提及要维持所谓地主或类似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所说的民是除君主之外的不特定对象,并非社会上的某一特定群体。臣民统统由君主控制,为君主效死尽忠。因此,深受法家思想影响的秦律(或后世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历代法律)从未确立以‘地主阶级’为权利主体的土地私有制”(第44页)。
“基于上述土地权利状态的特殊性,历史上王朝的赋役征敛从来不是依据官、民之间的协商――‘先同意后纳税’,并以王朝提供较完善的‘公共产品’为大致对价,重要原因就在于这种赋役征敛的理念并不基于严格的私人土地所有权,而是基于土地由王朝终极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共识,向‘持有王朝土地的人’分享(即强占)土地的产出利益。”(第82页)而在西欧封建社会,“国王靠自己的收入生活”是一个基本原则。征税必须出于公共事务,且必须“向征税对象说明理由,在取得理解的基础上,进而商议征收数量、方式”(第29页),此即所谓“征税协商制”,由其衍生的“没有代表不纳税”的理念成为西方宪政思想的基石。进入近代以后,西方的社会契约理论更是将公权力的产生与对私人财产的保护紧密相连,几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revolution”都以统治者强行征税为导火索。这不仅在传统中国社会匪夷所思,就在当今中国社会恐怕也堪称孤响。
当然,不容否认,“在传统中国不存在国家统一的私有财产权利制度的背景下,各种民间规则成为界定私人土地权利的制度替代”(第68页)。这些民间规则在事实上起到了确立和保护私人土地权利的作用。但是,这种通过民间规则确立和保护的私人土地权利“一直不是绝对的,其合法性根基仅在于有据可查的契约文书以及可供寻根问底的契约之链。私人的土地权利不是可以经过登记、获得排他性的物权形态,而是表现为由一系列契约文书构成类似于债权的外在表现形式……所有的对象与其说是‘物’,不如说是一种‘经营权’,因为转移和持有的始终是眼下的经营收益行为,同时,土地所有权本身并没有成为国家的一种制度”(第71~72页)。这种“类似于债权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相当高昂的成本。比如,由于权力机构不承担对土地权利的登记(或公示)义务,一旦地契灭失,“将引发他人侵蚀原权利人的土地,从而陷原权利人于不利处境”(第73页)。更何况正如本书所援引的周其仁的观点:“这里通行的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特殊规则面前各各特殊”(第69页)。因此,虽然不排除某些具体的制度实践可以被民法吸收,但这类民间规则在规范层面上根本不可能为现代民法提供资源,继受外域法律是中国民法建设的唯一可行之路。
在此不妨大段抄录作者的呼吁:“历经对传统中国‘私有制与所有权’的长时期清算,人们对私有财产制度的反感及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漠视积重难返。当今,人们对财产权利的保护仍很难跨越对私有制的认识障碍。对公有制与私有制不同偏好的思维定势,仍阻碍着法学界对历史真实的认识及寻找契合国情的法治建设之路。1982年中国宪法首次规定‘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经过漫长的历程,‘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于2004年3月才出现在新修订的宪法中。而这,也还仅仅代表法律观念的初步转变!”(第101~102页)
 《赫胥黎传》,〔英〕默里著,夏平、吴远恒译,文汇出版社2007年1月版,29.00元
《赫胥黎传》,〔英〕默里著,夏平、吴远恒译,文汇出版社2007年1月版,29.00元
同为二十世纪“反乌托邦”的代表作家,今天看来,赫胥黎似乎比奥威尔更了解人性。本书披露,赫胥黎在收到奥威尔寄赠的《一九八四》后回信表示很欣赏这本书,但同时认为自己的《美妙新世界》更有预见性――未来的寡头统治者会通过广告和洗脑确保人民“心甘情愿被奴役”,这比像奥威尔描述的那样残忍地践踏人民更高明、也更省力。(第241、363页)
不过,“反乌托邦作家”这个标签远不足以概括赫胥黎的生平和创作。出于家学渊源,他在骨子里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智识传统,“对那些在艺术和科学之间设立障碍的人不屑一顾,因为他知道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求知方式”(第8页)。他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主张全神贯注“察看”隐形的上帝,甚至为此在五十年代初率先尝试致幻药物。他在晚年又写了一本“好的乌托邦”小说《岛》,作为对《美妙新世界》的平衡。
 《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岳永逸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1月版,35.00元
《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岳永逸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1月版,35.00元
1949年以后,原本位居“下九流”之列的天桥街头艺术被规训、雅化,成为新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但从此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力。盖因这种底层血统的文化惟有在特定的狂欢化的“空间”里,通过一系列特定“仪式”和“规矩”的保障才有可能发扬光大,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书不仅翔实地论述了天桥街头卖艺文化的历史脉络、传承机制和博弈规则,而且深刻思辨了人的“异化”与文化传统式微之间的关系,读之令人感慨。
 《发现古脉: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李建民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版,58.00元
《发现古脉: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李建民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版,58.00元
本书在解读大量中医脉学典籍、尤其是马王堆脉书、张家山脉书等新近出土文献的基础上,将传统针灸疗法的根源追溯至先秦文化的数术宇宙观。作者指出,虽然诸如气、阴阳、感应、心包、三焦、命门等概念都不乏身体经验的基础,但将这些身体经验整合成体系性的脉学,其实有赖于经验之外的“意识形态”因素的介入。“换言之,经络体系不是长期经验累积而得,而是相反,即先有脉的概念再逐步证成。而数术模拟的思维方式在此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第271页)。“人体是小宇宙,它是模拟自周秦之时刚成形的数术式宇宙。因此,方技家以数术天学为模型,与其类比来把握人体的构造与机能,并进一步体系化。这是中国医学的天人密冥观……脉学的体系化是紧随周秦天学突破的一个过程”(第159页)。
那么,这是否等于宣告中医不“科学”呢?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中医的思考和论证方式是“反溯正当理由(retroductive warrants)”,其论证虽然难以被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比如西医――所接受,但却能在中医共同体内部形成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知识系统(见“大陆版序言”)。――因而若以融贯论的科学哲学立场视之,称其为广义的“科学”似乎并无不可。真正不科学的反而是那种貌似“科学”的以西医的概念体系和实验数据来“证实”中医理论的做法,不光走上了实证主义的死路,更肢解了中医在历史中形成的知识规范。时下国内关于中医存废论战方殷,此书对此提供了关键性的证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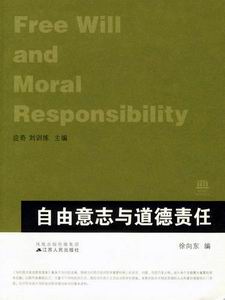 《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徐向东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40.00元
《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徐向东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40.00元
“自由意志”一向是西方哲学界关注和论争的焦点。这个概念意味着至少有某些人类行为不是由外部力量,而是由行为者自主决定的。不过,正如许多看似显而易见的直觉一旦诉诸哲学论证便难免漏洞百出一样,对自由意志的正面辩护也一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困境,因为它要求人的行为在某些方面是反因果关系的。而如果不把这种反因果关系的自由与毫无意义可言的随机性等量齐观的话,那么就势必要求“设定某个东西,这个东西把过去与未来联系在一起,但自身又不受自己的过去的限制,并且与自己的过去足够紧密地有关,以便保证个人的同一性与责任之间的联系。这非常类似于假定一个给世界意义内容和道德的神”(第29页)。――历史上确实有很多哲学家出于对自由意志的信念最终走向了宗教,但收入本书的若干当代英美分析哲学家的论文却启发读者直面如下问题:如果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幻象,并且我们承认这一点,结果会怎样?
事情并不像自由意志的信奉者设想得那样糟糕。人们之所以赋予自由意志这个形而上的概念如此的重要性,主要还是因为相信如果一个人的某项行为不是出于自由意志,那么他就不必对其承担道德责任。然而,人类的任何过失和罪行都可以被证证有词地论证为是由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甚或命运因素所决定的,因此这种认为道德责任有赖于自由意志的观点其实隐含着在实践中取消道德责任的危险。真相很可能是:“人们因为道德责任的原因而必须具有形而上的自由这种信仰,与我们早先相信人们必须属于正确的部落、种族、宗教一样,是一个明显的错误”(第36页)。――那么应该把道德责任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呢?一个合理的建议是:“从所有被决定的人类行动中挑选出那些我们在日常情形下会说它是出自我们的自由意志的行动……即使这些行为是被决定了的,但我们也对其负有责任”(第32页)。换言之,兜了一个大圈子,改变的只是我们对道德责任的界定和理解,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标准和实践。
